三松堂下,一个哲学家的“自白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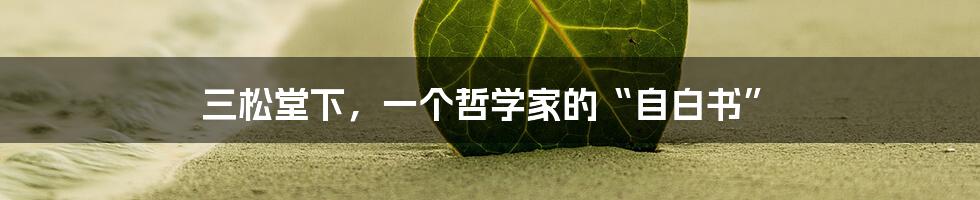
一、从中州“土包子”到西洋“博士”
我骨子里,是个河南唐河的“土包子”,从小脑子里装的都是“四书五经”“子曰诗云”。那时的我,觉得天下的道理,老祖宗都说明白了。可后来,时代变了,光靠这些老道理,似乎镇不住场子了。于是,我跟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,一头扎进了新学问里,还漂洋过海,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跟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先生念书。
那真是一次“开天眼”的经历。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思想也可以像做实验一样,讲究逻辑、证据和方法。那时候年轻气盛,总觉得找到了“终极武器”,要用西方的逻辑手术刀,来给中国文化这个几千年的“老病号”动一次大手术,让它脱胎换骨。这个想法,现在看来有点天真,但当时的我,是真诚的。
二、我的“哲学大厦”:《贞元六书》
回到国内,在西南联大那段艰苦却思想无比活跃的日子里,我开始了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——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。我想干什么呢?说白了,就是想给内忧外患的中国人,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。这个家园,地基得是中国的,但砖瓦、钢筋得用上现代的、世界的材料。
于是,我吭哧吭哧地写了《新理学》《新事论》《新世训》等“贞元六书”。我试图把宋明理学的那套“境界”说,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重新包装一遍。我自以为搭建起了一座宏伟的哲学大厦,从个人修养到社会理想,一应俱全。人们可以在这座大厦里,既有理性又有情怀,“诗意地栖居”。那是我学术生涯中最自得、最意气风发的几十年。
三、时代列车上的“补票”乘客
可没想到,时代这趟列车,在1949年之后,突然换了个方向,还大大提了速。我这个老学究,拎着旧时代的行李,拼了老命想挤上车,生怕被甩下去。人家说,你过去的思想都是“封建糟粕”,得“洗心革面”,脱胎换骨。
于是,我开始了我漫长的思想“改造”过程。这个过程,怎么说呢?就像是让一个打算盘的老师傅去学写代码,脑子里的线路都得重接过。疼,而且经常“短路”。我写了无数的检查,用新的尺子反复丈量自己过去的一切,试图否定昨天的我。
比如在那场著名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中,我被推上台去讲“儒法斗争”,用我研究了一辈子的儒家来“反”儒家。现在回看,那是一个老书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,一次尴尬而又必然的“转向”尝试。我像一个迟到的乘客,总想给飞速前进的列车补张票,证明自己没掉队。这种急切,让我说了一些今天看来需要深刻反思的话,也做了一些现在看来颇为滑稽的事。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弯路,也是我自述里最需要“自白”的部分。
四、重返书斋,最后的“作业”
风浪总有过去的时候。晚年,我又回到了我的书斋“三松堂”。人是老了,但心里那点“哲学癖”还在。我决定做最后一件事:重写一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。
这次重写,和年轻时完全不同了。我不再仅仅是做一个客观的学问家,而是把我这一辈子走过的弯路、摔过的跟头、经历的思想斗争,都融入了进去。一部哲学史,其实也是一个哲学家心灵的“忏悔录”。我试图用更宽广的视野,去理解历史,也理解自己。
我不知道自己最终解开了多少难题,但起码,我把笔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。或许,对于一个搞哲学的人来说,追求真理的过程,远比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更有意义。我这一生,不过是这个漫长求索过程中的一个标本罢了。
兴趣推荐
-
胡适是20世纪中国一位杰出的作家、思想家、文学评论家、学者、教育家和外交家。
3年前: 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。他以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广泛的研究,以及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而闻名。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,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。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奋斗,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。
-
从“世界大史”到“中国哲学史”,冯友兰的跌宕人生
2年前: 冯友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、教育家,曾任北京大学校长,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,国际哲学学会副会长等职。他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,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冯友兰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,他从一个平平无奇的乡下少年,成长为一位享誉世界的哲学大师,其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都耐人寻味。
-
陈来:学贯中西,思想之光
1年前: 提起陈来,人们脑海中浮现的,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思想巨匠,一位以“中国思想史”为毕生研究方向的学者,一位以严谨治学、诲人不倦著称的师长。他用一生时间,探索着中国思想文化的深邃奥秘,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-
冯友兰:从“中国哲学史”到“中国哲学”
1年前: 冯友兰,这位被誉为“中国哲学史之父”的大家,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,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哲学遗产。他的“中国哲学史”著作,如同打开一座宝库的大门,将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展现在世人面前,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化有了更深层的理解。
-
刘师培:从“经学大师”到“革命先驱”
1年前: 刘师培,一个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交汇的时代里,以其深刻的学识与坚定的信念,在学术界和革命运动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传奇人物。他既是“经学大师”,又是“革命先驱”,这一看似矛盾的身份,折射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。今天,让我们一起走进刘师培的时代,探寻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,感受他思想的魅力,以及他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