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魈不是狒狒:聊聊猴界“彩妆大师”和它那位“平平无奇”的亲戚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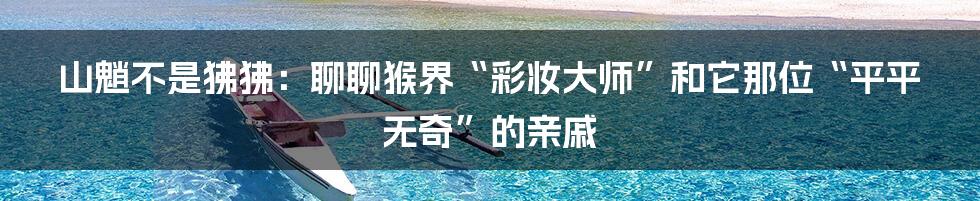
## 一、我是山魈,不是“花脸狒狒”
请允许我先为自己正名:我,山魈(学名:Mandrillus sphinx),是猴子,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猴子。我的名片,就印在我这张独一无二的脸上。你瞧瞧,这道从鼻梁延伸到嘴角的鲜红色,配上两颊深邃的天蓝色隆起,是不是感觉像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,还顺手给我画了个京剧脸谱?这可不是为了好看,这身“彩妆”是我的地位和荷尔蒙水平的象征。颜色越鲜艳,说明我在猴群里的地位越高,越能吸引异性的目光。
除了脸,我的另一个“亮点”在……嗯,身后。我的臀部也是一片五彩斑斓的景象,颜色和脸部遥相呼应。这套“前后双色皮肤通讯系统”非常高级,无论是求偶、示威还是表达情绪,都能一目了然。
我生活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雨林里,喜欢成群结队地活动,一个大家族(我们称之为“部落”)可以有上百甚至上千名成员,浩浩荡荡地在林间穿行,那场面,相当壮观。别看我长得“艺术”,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杂食主义者,水果、昆虫、小型脊椎动物,来者不拒。还有,我那长达6.5厘米的犬齿可不是闹着玩的,连花豹见了都得掂量掂量。
## 二、我的远房亲戚——狒狒
现在,让我们把镜头转向我的亲戚——狒狒(Papio属)。首先在长相上,它就“朴素”多了。狒狒的脸主要是肉色或灰黑色,没有我这么炫酷的色彩搭配。它们的脸更长,看起来有点像狗,所以有个外号叫“狗头猴”。
其次是生活环境。我喜欢潮湿阴暗的雨林,而狒狒老兄们则更偏爱开阔的稀树草原和半沙漠地带。它们是机会主义者,适应能力极强,经常能在非洲的各种纪录片里看到它们的身影。
再来说说那位家喻戶晓的“拉飞奇”长老。严格来说,它是个艺术加工的产物。它的彩色面孔和臀部,灵感100%来源于我(山魈),但它却长了一条狒狒标志性的长尾巴(我的尾巴很短,几乎看不见),而且生活在狮子王的荣耀石那种稀树草原环境里。所以,拉飞奇可以看作是一个“山魈脸、狒狒身”的混血明星。
## 三、我们为什么总被搞混?
这桩“冤案”的根源,主要有三点:
1. 血缘关系近:我们都属于猴科(Cercopithecidae)下的同一个亚科,是实打实的近亲,体型也都比较大,习惯在地面活动。
2. 曾经的分类:在早期的生物学分类中,我确实曾被归入狒狒属(Papio*),后来科学家们经过深入研究,才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异足够大,于是把我独立出来,成立了山魈属(*Mandrillus)。
3. 俗称的模糊性:在中文语境里,“狒”字常常用来形容一些体型较大、相貌凶猛的猴子,久而久之,“山魈”和“狒狒”就容易被口头语混为一谈,成了“山魈狒狒”这个模糊的组合。
简单总结一下区分我们的“傻瓜”方法:看到脸上红蓝相间、五彩斑斓的,那是我,山魈;看到一张长长的“狗脸”,颜色比较单调,在草原上晃悠的,那是狒狒。记住这个口诀,你就能在朋友面前秀一把你的动物学知识了!
## 四、不只是脸蛋,我们也很重要
无论是色彩斑斓的我,还是看似普通的狒狒,我们都在自然生态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我们通过取食果实,帮助植物传播种子,是名副其实的“森林园丁”和“草原播种机”。
然而,令人担忧的是,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非法盗猎,我的种群数量正在下降,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(IUCN)列为“易危”物种。我这张引以为傲的脸,也成了某些人眼中的“战利品”。
所以,下次当你再看到我或者我的亲戚狒狒时,希望你不仅能准确地叫出我们的名字,更能意识到,我们每一个独特的生命,都是这个蓝色星球上不可替代的宝藏,值得被了解和保护。
兴趣推荐
-
猩猩小庞:动物界的“小网红”,背后的故事与思考
3年前: 小庞,一只生活在重庆动物园的雄性黑猩猩,因其憨态可掬的外表和聪明的表现,在社交媒体上走红,成为动物界的“小网红”。小庞的走红,引发了人们对动物保护、动物福利、以及动物与人类关系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。
-
跳梁小丑是什么生肖:十二生肖幽默趣谈
3年前: “跳梁小丑”一词常用来形容那些行为荒唐、哗众取宠之人。十二生肖中,也有不少生肖与“跳梁小丑”有着不解之缘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!
-
人畜和谐,共生共荣
3年前: 人与动物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关系,动物是人类的朋友,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伙伴。然而,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,人与动物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,人类对动物的伤害也越来越大。我们要提倡人畜和谐,共生共荣,还动物一个清洁的家。
-
探索豢养的艺术:从萌宠到畜牧,你了解多少?
3年前: 豢养,作为人类与动物之间最古老的互动形式之一,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。从可爱的萌宠到重要的畜牧业,豢养的艺术跨越了物种界限,谱写出一曲动人的和谐篇章。
-
皮草网:解密时尚与动物保护的交织
3年前: 皮草网,一个由动物皮草制成的庞大网络,将时尚与动物保护紧密相连。本文将带你走进这个争议不断的领域,探索皮草背后的故事。
-
皮毛行情,趣谈裘皮业的行业冷暖
3年前: 在时尚界,皮毛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一件优质的皮草大衣不仅能彰显穿戴者的品味与身份,还能为其带来温暖与舒适。然而,近年来随着动物保护意识的增强,皮草行业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争议。在本文中,我们将带领大家走进皮毛行业,一探究竟它的冷暖变迁。
-
如愿以偿打一生肖
3年前: 中华民族素来有收藏生肖的习惯,生肖里藏着十二生肖动物的形象,在十二生肖文化中,人们常以各自属相的灵兽作为护身符,借以祈求好运与平安。其实,生肖文化不仅如此,它还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那么,“如愿以偿”这个成语与生肖之间有什么关联呢?
-
最小品种鹿诞生,萌化人心!
3年前: 近日,世界上最小的鹿诞生了!它只有20厘米高,重约2公斤,就跟一只小猫差不多大。难道我想养宠物还不需要特意出门了?
-
心猿意马指的是什么生肖?
3年前: 在十二生肖中,有一个生肖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心猿意马,难以集中注意力。这个生肖就是——猴。
-
兔毛皮草:时尚还是残酷?
3年前: 兔毛皮草是一种由兔毛制成的皮草,因其柔软、保暖等特点,一直以来颇受人们喜爱。但在另一方面,兔毛皮草的生产也备受争议,动物保护组织认为这是一种残忍的行为。那么,兔毛皮草到底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残酷呢?
-
皮草品牌:奢华、高贵与争议的交织
3年前: 皮草,一种兼具奢华与争议的时尚元素,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一直备受推崇。皮草品牌,作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,以其精湛的工艺、优质的皮草材料和独具匠心的设计,向世人展示着皮草的魅力。然而,皮草品牌也一直伴随着争议,从动物保护到环保问题,无不让皮草品牌处于风口浪尖。
-
理查·基尔:从好莱坞到《人鬼情未了》,一段浪漫的旅程
3年前: 理查·基尔,一位出生于美国费城的好莱坞演员、制片人和活动家,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,在全球影坛享有盛誉。从《美国舞男》到《人鬼情未了》,他用一个个经典的角色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。今天,让我们一起走进理查·基尔的世界,去探索他的演艺生涯和传奇故事。
-
2021年晚立秋热死牛:大自然的无情考验
3年前: 2021年,中国北方出现了罕见的晚立秋高温天气,导致多地牛群出现中暑死亡的情况。这起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气候变化和动物保护的关注。
-
“一五一十”打一生肖,猴机智,听我聪明的推理!
3年前: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谜语:“一五一十”打一生肖。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什么呢?如果你还没想出来,那就快来听听我的聪明的推理吧!
-
十二生肖中的百变之王
3年前: 在十二生肖中,有一种动物以其千姿百态而闻名,它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外表,融入不同的环境中。这种动物就是猴。
-
八面玲珑是什么生肖?
3年前: 在十二生肖中,有一位小动物非常擅长交际,八面玲珑,深谙人情世故,它就是——猴。
-
喜怒无常是什么生肖?
3年前: 众所周知,十二生肖与我们息息相关,不同的生肖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。今天,我们就来聊聊喜怒无常的生肖。
-
三阳开泰指什么生肖?
3年前: 三阳开泰是一个成语,也是一个吉祥的寓意。那么,三阳开泰是什么意思呢?它又指的是什么生肖呢?带着这些疑问,我们一起走进三阳开泰的世界吧!
-
四面八方生肖大亨
3年前: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有趣的问题,四面八方,这个成语有什么对应生肖呢?听上去摸不着头脑,一起来看看吧!
-
用形容词猜一生肖:獐头鼠目
3年前: “獐头鼠目”这个成语通常用于形容一个人长得贼眉鼠眼,为人狡猾奸诈。我这里用“獐头鼠目”做一生肖谜题,猜一下打个什么生肖。